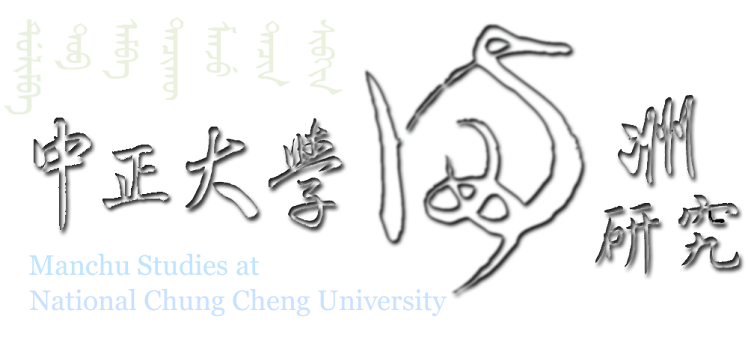在《乾隆帝》一書中,歐立德說大清「國名在滿語中是Daicing,它在滿語和蒙古語中均為「戰士」之意」(青石譯,2014,頁78; Elliott, 2009, p. 55.)。不過,大清國即「戰士國」之論並不是歐立德所創,首先提出這個看法的是義大利學者斯達理(Giovanni Stary)(喬.斯達理,1988,頁18)。[1]歐立德採用斯達理的見解是為了説明大清不是中國王朝的延續,而是一個內亞帝國。對此,李勤璞(2016)指出「關於大清國號(daicing gurun)的議論(78頁),涉及滿文、蒙古文知識和明清史,此處不作討論」,言下之意,大清國即「戰士國」是錯誤的。有關這點,本文作者也有同感。[2]
首先,滿文daiicing一字,除了表示是大清的滿文國號外,並沒有「戰士」之意,「戰士」,滿文作afasi(安雙成,2007,頁1354),cooxai niyalma等(Norman, 2013, pp. 60, 66)。[3]因此,滿文daiicing與蒙古語dayičin(戰士)並不是同源詞。蒙語dayičin由dayin(戰)+či+n(人們)組成(Nicholas Poppe, 1974, pp. 40-41, 72),指的不完全是「戰士(warrior)」,且更有「好戰(者)」之意(內蒙古大學蒙古學研究院蒙古語文研究所,1999,頁1122; Lessing, 1982, p. 222);滿文Daiicing則由「大+清」組成。
滿人入關前受漢人文化影響,皇太極時國號即稱大清。大清乃源自傳統中國國號的書法,如大明、大宋、大唐等。[4]即便明代的外國人如利瑪竇也知道大明乃大加上當朝國號而成(何高濟譯,2001,頁6)。值得注意的是12世紀的女真人所建立的國號也採用同樣「大+國號」的漢人模式,稱作大金,女真文作/amba-an antʃu-un/,[5]而「遼」,滿文寫作Daiiliyoo, 「元」則寫作Dai Yuwan.。[6]嘉慶二十四年滿文《太祖高皇帝本紀》上、下卷(Taiizu Dergi Xôwangdi–i ben-gi bithe,,dergi、fejergi debtelin)鈔本,於書前首頁,「大清」寫作Amba Cing Gurun-i ben-gi bithe,書後末頁則寫作Daiicing Gurun-i fuqjin ben-gi bithe (圖2),可知Daiicing即Amba Cing,亦即「大清」,不是「戰士國」[7]
正因為「大+國號」已是中國傳統書寫國家稱號的習慣,因此在清代跟各國簽訂的條約中,往往將大清國與「大某某國」並舉,作對等處理。1844年,道光皇帝給美國泰勒總統(President John Tyler)的國書便稱中國做Daiicing Gurun。(圖3) 清末,國書中的滿洲國號仍然堅持用此書法。不過,因為滿文衰落,漢化已深,大清國號變成了架床疊屋的Amba Daiicing,即「大大清」,[8]而忘了Daiicing的Daii-的原來意義就是「大」。[9]例如,光緒31(1905)年的國書中,相對於大英國Amba Yeng Gurun,中國便自稱做Amba Daiicing Gurun。(圖4)
國書中出現的Amba Daiicing Gurun國號所反映的漢化影響,從其滿漢文的對譯也能略窺一二。自滿人入關後,大清的詔令文書,包括遺詔,大都是先寫漢文後譯滿文(甘德星,2014,頁111),而愈往後愈是如此。在國書中,「大英國」一詞,滿文按照漢文,翻作Amba Yeng Gurun,而非如康雍時期,按照俄文,將之音譯作Anggiyalski(昂假爾斯奇)(今西春秋,1964,頁281、353),或如乾隆時,按照英文漢文對音「英吉利」,將之音譯作Ing-gi-lii Gurun(莊吉發,1989,頁81)。
從上引二封國書中,所謂大清國大皇帝向泰勒總統(伯理璽天德)[10]或大英國皇帝問好一句,其滿文部分,分別依漢文語順譯作Daiicing Gurun-i X
ôwangdi fonjime. Be-lii-hi-tiyan-de saiiyôn(行1─2),及Amba Daiicing Gurun-i Amba X
ôwangdi gingguleme fonjime. Amba Yeng Gurun-i Amba X
ôwangdi-de saiin(行1─2)。兩者一為問話句,一為陳述句,但句法皆不正確,動詞fonjime實應置於句末而非句中。[11]1908年大清國致俄羅斯的國書可為佐證。(圖五)其時雖為清末,但仍有少數精通滿文之人。國書中,大清國大皇帝向外國元首問好的開首套語,司其事者將之譯作Amba Daiicing Gurun-i Amba X
ôwangdi gingguleme Amba Oros Gurun-i Amba X
ôwangdi-de saiin-be fonjiki(Pang & Pchelin, 2013, pp. 244, 246, 247)。其滿文譯文,不但主謂語分明,而且謂語部分嚴格遵從滿文的賓動結構書寫,沒受漢文干擾。句子的主語是Amba Daiicing Gurun-i X
ôwangdi,而謂語則是由gingguleme Amba Oros Gurun-i Amba X
ôwangdi-de saiin-be fonjiki構成,其中的賓動結構saiin-be fonjiki是謂語的核心詞組,被gingguleme修飾,並與前面作為補語的Amba Oros Gurun-i Amba X
ôwangdi-de緊密相連,表示問好的對象。
《故宮俄文史料》錄滿檔十件,其中二件為康熙年間索額圖與俄國之間的往來文書,其文曰:(一)Oros-i Argut Xoton-i da So-fiya-lo-fu. musei dorgi amban Songγotu-de qôwaliyasun-i doroi saiin-be fonjime alibume unggihe Oros bithe-be ubaliyambuxa Manju bithe emke;(二)Dorgi amban Songγotu-de. Oros-i Mos-ke-wa Xoton-i An-de-ri-i qôwaliyasun ojoro jalin. saiin-be fonjime alibume unggihe. Oros bithe-be ubaliyambuxa Manju bithe emke(王之相、劉澤榮繙譯,1936,頁193、219;Walravens, 1996, pp.118.1-119.4)(圖6)。[12]可見,清代初期漢化尚未深時,敬問對方安好的典型句式莫不如此。
──────────────────────
[1]同文英譯見Stary, 1990, p.114.
[2]李勤璞未幾即續作〈駁斥歐立德:關於清朝國號的再討論〉,文載《文化縱橫》2017年第6期,其所用理據雖與筆者引用的不盡相同,但結論一致,可相互參照,如文中頁126─27,李勤璞引用著名蒙古學者薄音湖的見解,指出明末蒙古人名中的dayičing(大成、歹成、岱青、歹青、戴青)一詞乃源自漢文「大」及「誠」,並無戰士之意,即為筆者所不及見。
[3]滿文戰士尚有daiin-i xaxa一語(Norman, 2013, p. 66),其中的daiin不錯是借自蒙文的dayin,但和滿文daiicing的daii-無關,詳見文內討論。
[4]《湧幢小品》中的「國號」條云:「國號上加大字,始於胡元,我朝因之,蓋返左袵之舊,自合如此,且以別於小明王也。其言大漢、大唐、大宋者,乃臣子及外國尊稱之詞」(朱國禎,1959,頁22)。
[5]金啓孮,1984,頁224。在清代,12世紀的金朝,滿文多意譯作aiisin,如《金史》、《欽定遼金元三史語解四十六卷》。見黃潤華、屈六生,1991,頁163:0669;盧秀麗、閻向東編,2002,頁223。
[6]黃潤華、屈六生,1991,頁162:0668、頁163:0670。Daiiliao也可分寫作Dai Liyoo(如《欽定遼金元三史語解四十六卷》),見盧秀麗、閻向東編,2002,頁223。
[7]同樣意見也見於張雅晶,2014。張文另指出大清亦稱皇清,皇清與蒙文dayičin在音義上更無關係。見張雅晶文,2014,頁124-125、128。
[8]有趣的是現居臺北的錫伯老人廣定遠也誤用了Amba Daiicing Gurun一詞來指稱清朝,流毒之深,見於今日。見張華克,2005,頁5。
[9]在清代的蒙文文獻中,大清國稱做Dayičing ulus,而不是Yeke Dayičing ulus(大大清國),如蒙文《清太祖實錄》之稱作Dayičing ulus-un tayizu degedű quwangdi-yin maγad qauli,可以為証。
[10] 在道光致美國泰勒總統的國書中,Be-lii-hi-tiyan-de (伯理璽天德)一詞中tiyan字的n沒有加旁點,但光緒致大法國Be-lii-hi-tiyan-de 中tiya.n字的n則加了旁點,以避載湉(Zai Tiyan)諱(安雙成,1993,頁1146)。林士鉉以為這個加了旁點的.n是用來表示外來語是錯誤的(林士鉉,2015,頁58,圖十及頁62)。
[11]林士鉉認為這種不規範的滿文句法,是出於滿漢文為抬頭對齊而不得已的做法(林士鉉,2015,頁61)。這看法並不正確,因為若將致大英國或大法國國書第二行的gingguleme fonjime(敬問),移至第四行Amba X
ôwangdi-de saiin或Amba Be-lii-hi-tiyan-de -de saiin後面,以符合滿文文法,並不影響原來兩國元首稱謂對稱平衡的格式。
[12]Walravens書中的Mos-ka-wa應轉寫作Mos-ke-wa, bithe誤作bihe。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甘德星)
──────────────
文見
甘德星,〈孰是孰非:歐立德《乾隆帝》一書中滿文翻譯的商榷〉,《編譯論叢》第十二卷第一期(201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