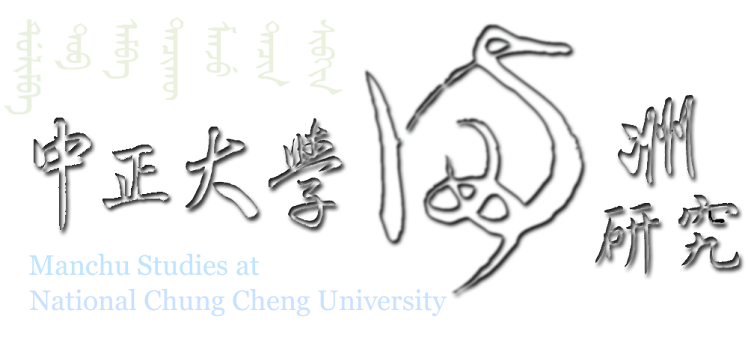作 者:【美】白彬菊
出版時間:2017-04-15
ISBN:978-7-300-24007-7
譯 者:董建中譯
定價:¥69.00
內容簡介
本書利用臺北和北京所藏漢文與滿文檔案,採用內外朝的分析框架,深入細緻地研究了清中期的軍機處。本書認為,軍需處—軍機房—軍機處三階段說不成立。軍機處有一逐步建立的過程,雍正時期的內廷機構是小規模、分立的,直到乾隆二年,才有了統一的、後來擁有廣泛權力的軍機處。非正式性的軍機處擁有法外活力,加之保密性、滿漢混合、人員兼職、頻繁戰事、皇帝熱衷巡幸、大臣們的野心等因素,使它能在行政、通信等諸多領域迅速擴張。結果是:內廷有從君主統治到大臣管理的轉型;君主的統治已離不開軍機處,君主專制統治讓位給了君主與大臣的合作;在決策上,大臣有可能限制君主的獨斷。嘉慶朝的軍機處改革,是在軍機處的主導下進行的,並未觸動軍機處的地位。軍機處對清朝的統治影響深遠。
本書利用臺北和北京所藏漢文與滿文檔案,採用內外朝的分析框架,深入細緻地研究了清中期的軍機處。本書認為,軍需處—軍機房—軍機處三階段說不成立。軍機處有一逐步建立的過程,雍正時期的內廷機構是小規模、分立的,直到乾隆二年,才有了統一的、後來擁有廣泛權力的軍機處。非正式性的軍機處擁有法外活力,加之保密性、滿漢混合、人員兼職、頻繁戰事、皇帝熱衷巡幸、大臣們的野心等因素,使它能在行政、通信等諸多領域迅速擴張。結果是:內廷有從君主統治到大臣管理的轉型;君主的統治已離不開軍機處,君主專制統治讓位給了君主與大臣的合作;在決策上,大臣有可能限制君主的獨斷。嘉慶朝的軍機處改革,是在軍機處的主導下進行的,並未觸動軍機處的地位。軍機處對清朝的統治影響深遠。
章節目錄
第一部分雍正朝分立的內廷:軍機處的前身
(1723—1735)
第一部分雍正朝分立的內廷:軍機處的前身
(1723—1735)
第一章雍正初年內廷的加強
雍正初年的外朝
雍正初年的內廷
雍正皇帝繼位時面臨的種種問題
雍正皇帝控制外朝的嘗試
規避外朝的雍正內廷
雍正初年的外朝
雍正初年的內廷
雍正皇帝繼位時面臨的種種問題
雍正皇帝控制外朝的嘗試
規避外朝的雍正內廷
第二章雍正的內廷助手:親王與大學士
怡親王允祥
張廷玉
怡親王允祥
張廷玉
第三章皇帝的內廷代理人
皇帝內廷代理人的發展
書面議覆
廷寄
皇帝內廷代理人的發展
書面議覆
廷寄
第四章為平准之役而設立的內廷下屬機構
戶部軍需房
大臣
戶部軍需房
大臣
第二部分乾隆內廷統一時期軍機處的建立與擴張
(1735—1799)
(1735—1799)
第五章總理事務王大臣時期內廷的轉型
(1735—1738)
清朝過渡班子的歷史背景
雍正內廷機構的統一
總理事務王大臣的人事安排
總理事務王大臣的職責
總理事務王大臣時期的變化
反對內廷壯大
從總理事務王大臣到軍機處
(1735—1738)
清朝過渡班子的歷史背景
雍正內廷機構的統一
總理事務王大臣的人事安排
總理事務王大臣的職責
總理事務王大臣時期的變化
反對內廷壯大
從總理事務王大臣到軍機處
第六章18世紀軍機處的結構
乾隆朝軍機處的鼎盛
軍機處的名稱與專用術語
軍機大臣
軍機處的行政職責
乾隆朝軍機處的鼎盛
軍機處的名稱與專用術語
軍機大臣
軍機處的行政職責
第七章軍機處下屬組織
軍機章京
軍機處滿伴
方略館
軍機章京
軍機處滿伴
方略館
第三部分結局
第八章嘉慶皇帝對軍機處的改革(1799—1820)
嘉慶改革的原因
嘉慶皇帝對軍機處的改革
嘉慶改革的原因
嘉慶皇帝對軍機處的改革
結語
軍機處設立時間問題
內廷轉型的主要階段
18世紀有利於軍機處成長的因素
可能阻礙軍機處成長的因素
嘉慶統治結束時的軍機處
軍機大臣與皇帝的關係
軍機處設立時間問題
內廷轉型的主要階段
18世紀有利於軍機處成長的因素
可能阻礙軍機處成長的因素
嘉慶統治結束時的軍機處
軍機大臣與皇帝的關係
附錄A雍正朝文件中的“部”
附錄B“辦理軍需大臣”的材料
附錄C雍正朝“辦理軍需大臣”“辦理軍機大臣”人名
附錄D雍正朝內廷滿章京
附錄E總理事務王大臣中的編纂人員
附錄F軍機處滿伴業務——對乾隆初年一個月滿文奏摺上報事項的考察
附錄B“辦理軍需大臣”的材料
附錄C雍正朝“辦理軍需大臣”“辦理軍機大臣”人名
附錄D雍正朝內廷滿章京
附錄E總理事務王大臣中的編纂人員
附錄F軍機處滿伴業務——對乾隆初年一個月滿文奏摺上報事項的考察
徵引文獻
索引
中文版後記
譯後記
索引
中文版後記
譯後記
精彩片斷
序言
本書描述的是18世紀時清朝(1644—1911)統治的重大轉型,許多中央機構合併為一個新的具有管理與協調職責的內廷樞密組織——軍機處。清初的皇帝與在京各種機構打交道,多能親力親為,處理當時相對不複雜的政務,僅有一些大臣和辦事人員在旁協助。清中期(1723—1820)這一轉型的結果是,數個分立的輔佐皇帝的集團合併為一個新的機構——軍機處,這一組織位於君主和中央各機構中間,是一個能夠處理清朝中期激增事務的實體。這一轉型對於最終擊敗西北邊疆敵對的蒙古人,以及乾隆皇帝十全武功的軍事勝利,都是重要的因素,十全武功將中華帝國的邊界推至歷史上的極遠(僅次於1206—1368年的元帝國,當時中國是該帝國的一部分)。鴉片戰爭(1839—1842)之後,這一富有經驗的班子要應對清朝最後五十年的種種緊急情況,包括大規模叛亂、皇帝幼沖、攝政體制以及西方日緊的入侵。可以說,有了18世紀從皇帝親理政務向君主—軍機大臣共治的這一轉型,才推動了清朝在中期達到盛世,並延續了自身存在,直至覆亡。
本書主要是探求18世紀這一轉型如何發生,何以發生;是什麼導致軍機處的形成並令其崛起,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淩駕于中華帝國的幾乎整個中央政府;在律令密如凝脂且對於大臣與官僚(ministerial and bureaucratic)間的黨爭極為敏感的行政環境中,一個新的高層機構何以被推至主導的地位。當我們放寬眼界,考察軍機處形成與發展的頭一百年歷史時,現有的軍機處起源諸學說——通常認為起源于雍正皇帝在位(1723—1735)的最後七年間,是否有助於我們對上述問題的理解呢?
本書主要是探求18世紀這一轉型如何發生,何以發生;是什麼導致軍機處的形成並令其崛起,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淩駕于中華帝國的幾乎整個中央政府;在律令密如凝脂且對於大臣與官僚(ministerial and bureaucratic)間的黨爭極為敏感的行政環境中,一個新的高層機構何以被推至主導的地位。當我們放寬眼界,考察軍機處形成與發展的頭一百年歷史時,現有的軍機處起源諸學說——通常認為起源于雍正皇帝在位(1723—1735)的最後七年間,是否有助於我們對上述問題的理解呢?
軍機處起源的雍正三階段模式
大多數對於軍機處在雍正朝發展的記載都承襲了清朝官方的觀點,這是從後來強大、集權的班子的立場往回看,描述的是公認睿智、洞察一切的雍正皇帝自覺地創建了這一強大、集權的內廷機構——英語稱為“Grand Council”(軍機處)。儘管這些分析稍有不同,但通常的看法是,早期的軍機處——其源起被認為是內閣的一個分支——有三個明確的發展步驟。起初是雍正七年(1729)的“軍需房”,它在內廷建立,接近皇帝以辦理針對西北準噶爾蒙古的戰爭。接著它變為中間階段的“軍機房”。最後成為強大的“軍機處”。所有這三階段被認為是在雍正皇帝統治期間的最後七年內完成的。
一個機構日益壯大並多次改名,這種描述存在著解釋上的困難。臺北“故宮博物院”莊吉發已經指出,“軍機房”一詞在雍正時期的文件中根本不存在。吳秀良在1970年出版的《通信與帝國控制:奏摺制度的發展(1693—1735)》一書中,也質疑了這種通行觀點。他在描述一個輔佐皇帝的小規模、緊密結合的集團時,發現這些人並不是應付西北戰事的這一不斷變化的機構的成員,他們確是在履行後來的軍機大臣的特有職責。這些輔佐皇帝的內廷人員,有時稱作“內中堂”,是皇帝的高級心腹,執行皇帝指派的一切任務。他們關切其他的內廷行政機構,但不是作為全職的成員,而是兼職的監管者。吳教授著作中的這一睿識,為理解雍正內廷的行政作用提供了至關重要的一步:它不是由單一、強大的機構所組成的,因此它與後世的軍機處並不完全相像。毋寧說,雍正內廷是由數個非正式、不具有法定地位的集團組成的,這種設計意在便於皇帝控制。
隨後,我自己從檔案中的發現完善了這一新的解釋框架。1970年代在臺北“故宮博物院”時,想到乾隆皇帝登極之後臣下會向他彙報情況,順此我發掘出了一份關鍵性奏摺,它暴露出上述通行解釋的又一缺陷。這份檔顯示,軍需房作為戶部堂官下屬部門創設之後,從未變更過名字,也未有任何形式上的變化,它以雍正七年時所被賦予的許可權和名字運作, 直至雍正皇帝統治結束。1980—1981年,我在利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的漢文材料時,發現反復提到另一內廷機構“辦理軍需大臣”,它創建于雍正八年末(1731年初),後來改名為“辦理軍機大臣”(有時也稱“軍機處”,滿文是Coohai nashūni ba)。這證明當時還存在著一個機構——遠不及後來的軍機處強大,卻有著相同的名字。像另兩個機構一樣,這個機構也是獨立存在,直到雍正皇帝統治結束。
1985年秋,我在北京參加一個研討會時,獲允查看新近整理的廷寄上諭、滿文奏摺和檔冊。這些提供了關於內廷心腹和辦理軍需大臣更進一步的細節材料:他們的職責、人員構成和組織結構。這些檔案的發現最終證實,雍正的內廷行政部門繼承了康熙內廷分立模式。雍正的內廷由分立的個人及小規模的機構組成,而不是一個統一的軍機處。這是本書第一部分所講的內容。內廷從分立到統一的關鍵轉型還要等到乾隆皇帝統治(1735年末—1795年)初年,這將在第二部分討論。
一個機構日益壯大並多次改名,這種描述存在著解釋上的困難。臺北“故宮博物院”莊吉發已經指出,“軍機房”一詞在雍正時期的文件中根本不存在。吳秀良在1970年出版的《通信與帝國控制:奏摺制度的發展(1693—1735)》一書中,也質疑了這種通行觀點。他在描述一個輔佐皇帝的小規模、緊密結合的集團時,發現這些人並不是應付西北戰事的這一不斷變化的機構的成員,他們確是在履行後來的軍機大臣的特有職責。這些輔佐皇帝的內廷人員,有時稱作“內中堂”,是皇帝的高級心腹,執行皇帝指派的一切任務。他們關切其他的內廷行政機構,但不是作為全職的成員,而是兼職的監管者。吳教授著作中的這一睿識,為理解雍正內廷的行政作用提供了至關重要的一步:它不是由單一、強大的機構所組成的,因此它與後世的軍機處並不完全相像。毋寧說,雍正內廷是由數個非正式、不具有法定地位的集團組成的,這種設計意在便於皇帝控制。
隨後,我自己從檔案中的發現完善了這一新的解釋框架。1970年代在臺北“故宮博物院”時,想到乾隆皇帝登極之後臣下會向他彙報情況,順此我發掘出了一份關鍵性奏摺,它暴露出上述通行解釋的又一缺陷。這份檔顯示,軍需房作為戶部堂官下屬部門創設之後,從未變更過名字,也未有任何形式上的變化,它以雍正七年時所被賦予的許可權和名字運作, 直至雍正皇帝統治結束。1980—1981年,我在利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的漢文材料時,發現反復提到另一內廷機構“辦理軍需大臣”,它創建于雍正八年末(1731年初),後來改名為“辦理軍機大臣”(有時也稱“軍機處”,滿文是Coohai nashūni ba)。這證明當時還存在著一個機構——遠不及後來的軍機處強大,卻有著相同的名字。像另兩個機構一樣,這個機構也是獨立存在,直到雍正皇帝統治結束。
1985年秋,我在北京參加一個研討會時,獲允查看新近整理的廷寄上諭、滿文奏摺和檔冊。這些提供了關於內廷心腹和辦理軍需大臣更進一步的細節材料:他們的職責、人員構成和組織結構。這些檔案的發現最終證實,雍正的內廷行政部門繼承了康熙內廷分立模式。雍正的內廷由分立的個人及小規模的機構組成,而不是一個統一的軍機處。這是本書第一部分所講的內容。內廷從分立到統一的關鍵轉型還要等到乾隆皇帝統治(1735年末—1795年)初年,這將在第二部分討論。
內廷—外朝模式與乾隆朝軍機處的壯大
關於雍正朝軍機處的起源問題,學者們的研究專著、文章有數十種之多,與此形成對比的是,軍機處在乾隆朝令人驚詫地崛起並權傾中央政府,迄今卻幾乎沒有研究。然而,人們對於清朝之前的類似情況有過描述,常常用以分析皇帝集團的內廷與官僚集團的外朝間的權力鬥爭。一方是皇帝、他的內府及私人樞密輔助班子;另一方是官員,他們把持著各部院,管理整個帝國。這些爭鬥各朝各代情況各異。強勢的皇帝能號令行政官員;強勢的官僚也會孤立皇帝,獨立管理國家。有些時期,爭鬥完全發生在內廷,宮中太監時常起著主導作用。然而,除黃培的作品外,絕大多數清史著述未能強調這種分裂對立。黃培敏銳地看到了早期軍機處“本質上”是“內廷”的一種“再創造”。事實上,內廷與外朝的劃分確實存在於清廷中樞。而且,這密切關乎軍機處的發展。
清朝大多數時期通行的兩種通信體系,為上述內廷與外朝的二分法提供了很好的例證,也提供了適用的研究之道。承襲明朝而來的本章制度在外朝盛行。這是一種公開、透明、有章可循的官僚政治管道,它的許多文件——報告以及對之批答的諭旨——最終會在邸抄上刊行。為了支持和進一步使用本章,外朝擁有自己的檔案庋藏部門,並利用這些檔案編纂實錄、國史等官書。
與本章制度不同,奏摺制度始於康熙朝,是皇帝的私人通信管道,檔需要保密,並僅在內廷和外省通信者間流通。對於奏摺的兩種主要正式批示,一是朱批,用皇帝專用的朱紅色書寫意味著這些批示出自皇帝之手;二是廷寄上諭。這些批示完全在內廷的圈子內書寫、交付、處理。在雍正朝,內廷也開始發展出自己的檔案庋藏之地,最初只是奏摺,後來有了其他類別的文件。在接下來的乾隆朝,授權軍機處可以自己編書,最有名的是方略,是利用內廷檔案編纂的。這一特殊的內廷通信體系在軍機處的這些發展中起著關鍵作用,為君主及其內廷大臣提供了保密管道,他們也因此可以接觸重要資訊。
內廷與外朝的種種差別同樣也表現在中央政府管理結構上。外朝官僚體系由主要的行政機構組成,大部分承襲明及以前諸朝。這些機構的主要任務是處理本章——這些檔來自全國各地,幾乎囊括了政務的所有重要方面。外朝依法運作,也就是說,行政法規支配著管理帝國的外朝人員,這對於理解外朝在18世紀的發展極其重要。
與承襲而來、基本沒有變化且依法行事的外朝機構不同,清初的內廷是皇帝特許的產物,而且每朝都有變化。例如,儘管雍正皇帝允許乃父的議政王大臣和南書房繼續存在,但很少使用它們,它們也就漸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他為自己的內廷設計的一個新方案,任命最高層親信一至四人組成高級輔佐大臣,以及兩個新的中層機構——戶部軍需房和辦理軍需大臣(上面已提到)。乾隆皇帝繼位,發生了另一重大的變化,雍正的三個內廷實體合而為一。辦理軍機處,即這一機構的舊有名字,被再次啟用,作為新合併機構的名稱(現在英語可以恰當地將它譯作“Grand Council”),成為主要的行政機構,直至清朝覆亡。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此後的清人及近現代的人都認為,強大、統一的內廷軍機處創建于雍正朝。現在我們知道,這種說法僅僅在機構名稱的意義上是正確的。
在本書中,我使用英文“bureaucrat”(官僚)、“bureaucracy”(官僚機構)——幾如雍正皇帝自己看待這些人一樣——來指稱龐大的外朝人員。而內廷上層官員,我稱為“ministers”(大臣,指某些大學士、尚書、侍郎,他們是皇帝籠絡的重點),這些人由皇帝特簡,差不多每天與皇帝接觸。儘管他們已變成了內廷侍臣,但雍正皇帝通過他們在外朝的兼職,指派他們管理外朝官僚機構。在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看來,這些人不是普通的外朝官僚,因此我也避免使用外朝的術語來描述他們。
如果我們將這項研究中的起因(也就是軍機處創設與成長的原因)僅僅視作皇帝長期謀劃發展內廷以及由此加強專制者統治能力的結果的話,那將是錯誤的。其他因素也促成了軍機處發展成為擁有兩百多人、指揮著帝國政府的一個大規模內廷組織。軍機處對於一種全面完備的通信管道的壟斷,在它的成長中起著重要作用,這同將內廷活動與軍機處擴張隱藏起來以避免外朝嫉妒和報復的保密性所起的作用一樣。時代的特殊情勢——雍正皇帝對外朝易於瀆職的擔心、軍事行動的需求,乾隆皇帝對巡幸的熱衷——也要求一個由大臣掌握的小規模、緊密團結的班子,而這些大臣是皇帝熟悉和信任的。大臣們的野心儘管難以測算,但也必須算作軍機處地位崛起的一個因素。
最後一點,內廷的非正式性——雍正的內廷尤其明顯——是軍機處成長的又一重要因素。雍正的新內廷機構,法條無明文規定,也無正式機構應有的名分。相反,他的三個內廷機構所起的作用超出了行政法規的規定,擁有我稱之為“法外活力”(the extralegal dynamic)的優勢條件。在乾隆朝,當這些機構結合起來挑戰存在已久的外朝機構時,這種不受法律羈絆的自由促進了它們的成長。軍機處的法外地位允許它採取新的行動,進行種種擴張,而行政法規禁止它的對手外朝機構如此行事。這種優勢條件的一個例證出現在第六章結尾處,那裏敍述的是軍機大臣兼職問題——這是由於軍機處自身沒有專任職位造成的。這些兼職大臣所承擔的一些外朝職責被轉移到了軍機處的轄下,從而擴大了它的職掌。兼職使得軍機處人員與整個京城官僚系統有了非正式的接觸,也使他們能接觸到廣泛、分散的資訊來源。由此帶來了耐人尋味之處:雍正皇帝發展內廷,但堅持使之弱勢、分立,不具有正式地位,屈從於他的意志,這反倒成為在接下來的乾隆朝軍機處如日中天的一個重要原因。
對此,讀者可能會問,在公認朕即法的專制情形下,怎麼會賦予法外活力的特權?皇帝若要改變內廷或外朝的法律安排,他肯定有權這樣做。
關鍵在於內廷和外朝相異的法律地位。政府的外朝機構是依行政法規建置的,一般來說要依照會典及會典事例行事。儘管君主可能隨意改變這些制度(的確有一些這樣的例子),但大多數情況下,皇帝還是尊重先例並聽從臣下的建言。可以說,外朝更多的是依法律和多數人的意見運作,而不是被迫接受皇帝粗暴的權力,儘管統治的言辭總是強烈地暗示著這種權力的存在。
相形之下,在18世紀初——也就是我們研究的起點——法律沒有對內廷做出限定。當時輔助皇帝的大小官員被認為是皇帝自己的人:由他任命,聽他指揮。在內廷沒有會典可以援引以挫敗君主的意願。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內廷不受法律約束,享有可以對抗外朝對手的靈活性。
第二部分所討論的是,成熟的軍機處在什麼地方符合內廷—外朝這一框架。它是一個效忠於清中晚期皇帝並促成他們專制計畫的私屬班子嗎?抑或它最終發展出了自己的利益所在,成為一個指揮官僚的外朝行政機構呢?換言之,進入19世紀,軍機處是皇帝的爪牙還是官僚機構的領袖?我的研究認為,在鬥爭中軍機處並未偏袒一方,而是抓住了雙方所提供的機會。它依然忠誠于皇帝,而同時又發展到可以指揮外朝的大多數機構。結果,內廷的優勢極大擴展,但這是大臣和君主二者都強大的優勢局面。專制統治的框架依然存在,但作為實現專制統治不可或缺條件的內廷業務及大臣技能的膨脹,削弱了君主全面管理和指揮政府的能力。結果,中央政府(內廷和外朝)以及外省多聽命於內廷這一新合併的機構。
清朝大多數時期通行的兩種通信體系,為上述內廷與外朝的二分法提供了很好的例證,也提供了適用的研究之道。承襲明朝而來的本章制度在外朝盛行。這是一種公開、透明、有章可循的官僚政治管道,它的許多文件——報告以及對之批答的諭旨——最終會在邸抄上刊行。為了支持和進一步使用本章,外朝擁有自己的檔案庋藏部門,並利用這些檔案編纂實錄、國史等官書。
與本章制度不同,奏摺制度始於康熙朝,是皇帝的私人通信管道,檔需要保密,並僅在內廷和外省通信者間流通。對於奏摺的兩種主要正式批示,一是朱批,用皇帝專用的朱紅色書寫意味著這些批示出自皇帝之手;二是廷寄上諭。這些批示完全在內廷的圈子內書寫、交付、處理。在雍正朝,內廷也開始發展出自己的檔案庋藏之地,最初只是奏摺,後來有了其他類別的文件。在接下來的乾隆朝,授權軍機處可以自己編書,最有名的是方略,是利用內廷檔案編纂的。這一特殊的內廷通信體系在軍機處的這些發展中起著關鍵作用,為君主及其內廷大臣提供了保密管道,他們也因此可以接觸重要資訊。
內廷與外朝的種種差別同樣也表現在中央政府管理結構上。外朝官僚體系由主要的行政機構組成,大部分承襲明及以前諸朝。這些機構的主要任務是處理本章——這些檔來自全國各地,幾乎囊括了政務的所有重要方面。外朝依法運作,也就是說,行政法規支配著管理帝國的外朝人員,這對於理解外朝在18世紀的發展極其重要。
與承襲而來、基本沒有變化且依法行事的外朝機構不同,清初的內廷是皇帝特許的產物,而且每朝都有變化。例如,儘管雍正皇帝允許乃父的議政王大臣和南書房繼續存在,但很少使用它們,它們也就漸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他為自己的內廷設計的一個新方案,任命最高層親信一至四人組成高級輔佐大臣,以及兩個新的中層機構——戶部軍需房和辦理軍需大臣(上面已提到)。乾隆皇帝繼位,發生了另一重大的變化,雍正的三個內廷實體合而為一。辦理軍機處,即這一機構的舊有名字,被再次啟用,作為新合併機構的名稱(現在英語可以恰當地將它譯作“Grand Council”),成為主要的行政機構,直至清朝覆亡。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此後的清人及近現代的人都認為,強大、統一的內廷軍機處創建于雍正朝。現在我們知道,這種說法僅僅在機構名稱的意義上是正確的。
在本書中,我使用英文“bureaucrat”(官僚)、“bureaucracy”(官僚機構)——幾如雍正皇帝自己看待這些人一樣——來指稱龐大的外朝人員。而內廷上層官員,我稱為“ministers”(大臣,指某些大學士、尚書、侍郎,他們是皇帝籠絡的重點),這些人由皇帝特簡,差不多每天與皇帝接觸。儘管他們已變成了內廷侍臣,但雍正皇帝通過他們在外朝的兼職,指派他們管理外朝官僚機構。在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看來,這些人不是普通的外朝官僚,因此我也避免使用外朝的術語來描述他們。
如果我們將這項研究中的起因(也就是軍機處創設與成長的原因)僅僅視作皇帝長期謀劃發展內廷以及由此加強專制者統治能力的結果的話,那將是錯誤的。其他因素也促成了軍機處發展成為擁有兩百多人、指揮著帝國政府的一個大規模內廷組織。軍機處對於一種全面完備的通信管道的壟斷,在它的成長中起著重要作用,這同將內廷活動與軍機處擴張隱藏起來以避免外朝嫉妒和報復的保密性所起的作用一樣。時代的特殊情勢——雍正皇帝對外朝易於瀆職的擔心、軍事行動的需求,乾隆皇帝對巡幸的熱衷——也要求一個由大臣掌握的小規模、緊密團結的班子,而這些大臣是皇帝熟悉和信任的。大臣們的野心儘管難以測算,但也必須算作軍機處地位崛起的一個因素。
最後一點,內廷的非正式性——雍正的內廷尤其明顯——是軍機處成長的又一重要因素。雍正的新內廷機構,法條無明文規定,也無正式機構應有的名分。相反,他的三個內廷機構所起的作用超出了行政法規的規定,擁有我稱之為“法外活力”(the extralegal dynamic)的優勢條件。在乾隆朝,當這些機構結合起來挑戰存在已久的外朝機構時,這種不受法律羈絆的自由促進了它們的成長。軍機處的法外地位允許它採取新的行動,進行種種擴張,而行政法規禁止它的對手外朝機構如此行事。這種優勢條件的一個例證出現在第六章結尾處,那裏敍述的是軍機大臣兼職問題——這是由於軍機處自身沒有專任職位造成的。這些兼職大臣所承擔的一些外朝職責被轉移到了軍機處的轄下,從而擴大了它的職掌。兼職使得軍機處人員與整個京城官僚系統有了非正式的接觸,也使他們能接觸到廣泛、分散的資訊來源。由此帶來了耐人尋味之處:雍正皇帝發展內廷,但堅持使之弱勢、分立,不具有正式地位,屈從於他的意志,這反倒成為在接下來的乾隆朝軍機處如日中天的一個重要原因。
對此,讀者可能會問,在公認朕即法的專制情形下,怎麼會賦予法外活力的特權?皇帝若要改變內廷或外朝的法律安排,他肯定有權這樣做。
關鍵在於內廷和外朝相異的法律地位。政府的外朝機構是依行政法規建置的,一般來說要依照會典及會典事例行事。儘管君主可能隨意改變這些制度(的確有一些這樣的例子),但大多數情況下,皇帝還是尊重先例並聽從臣下的建言。可以說,外朝更多的是依法律和多數人的意見運作,而不是被迫接受皇帝粗暴的權力,儘管統治的言辭總是強烈地暗示著這種權力的存在。
相形之下,在18世紀初——也就是我們研究的起點——法律沒有對內廷做出限定。當時輔助皇帝的大小官員被認為是皇帝自己的人:由他任命,聽他指揮。在內廷沒有會典可以援引以挫敗君主的意願。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內廷不受法律約束,享有可以對抗外朝對手的靈活性。
第二部分所討論的是,成熟的軍機處在什麼地方符合內廷—外朝這一框架。它是一個效忠於清中晚期皇帝並促成他們專制計畫的私屬班子嗎?抑或它最終發展出了自己的利益所在,成為一個指揮官僚的外朝行政機構呢?換言之,進入19世紀,軍機處是皇帝的爪牙還是官僚機構的領袖?我的研究認為,在鬥爭中軍機處並未偏袒一方,而是抓住了雙方所提供的機會。它依然忠誠于皇帝,而同時又發展到可以指揮外朝的大多數機構。結果,內廷的優勢極大擴展,但這是大臣和君主二者都強大的優勢局面。專制統治的框架依然存在,但作為實現專制統治不可或缺條件的內廷業務及大臣技能的膨脹,削弱了君主全面管理和指揮政府的能力。結果,中央政府(內廷和外朝)以及外省多聽命於內廷這一新合併的機構。
本書的安排
本書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雍正時期軍機處的起源,這時處於一位不信任擁有全權的組織的君主統治之下。這幾章(第一章至第四章)描述了雍正皇帝對於可能成為自己對手的替代權力中心存有猜忌,追求分而治之的政策,更願意直接與簡任的個人和小規模、非正式集團打交道,決不希望它們聯合,在內廷的心臟地區成為單一、強大的私人樞密班子。第一章,我描述了雍正皇帝繼位時所面對的內廷—外朝形勢,決意強化內廷顯然是為應對他所面臨的困難。第二章展現了如何逐漸使用兩位內廷親信來處理一系列高端任務。第三章,我解釋了他們二人是如何成為一個極小規模、無名的內廷高層管理梯隊——我稱之為“內廷代理人”(inner deputies)——的核心的。第四章是雍正朝研究的最後一章,描述了雍正時期為應付軍事行動而建立兩個下屬機構的過程。可以說,儘管雍正皇帝建立了作為軍機處前身的眾多內廷組織,但他總是令它們分立,並極力避免產生一個配得上譯作“Grand Council”(軍機處)的單一、強大的組織。
並非所有的讀者都會對第一部分的細節感興趣,許多人會直接翻到第二部分,這部分描述的是18世紀成熟的軍機處。與第一部分集中論述短暫的十三年不同,第二部分包括乾隆皇帝在位的六十年,另加禪位後的三年,因此不能刻畫太細。作為導言性質的第五章,敍述了雍正時期三個非正式內廷機構在服喪期合併為過渡性的“總理事務王大臣”,並解釋了雍正時期的一個內廷機構的名稱“軍機處”如何在乾隆初年再次被使用,作為新的擴大了的內廷機構的名稱,之後這一機構被譯作“Grand Council”是合適的。接下來的第六章和第七章,探討的是乾隆皇帝統治六十多年間的軍機處。這裏對軍機處的發展做了一些敍述,但對於它成長過程中的迂回曲折則少有細節描述。這幾章主要用力之處是要表明中央政府文牘事宜劇增,以及由此帶來的乾隆時期軍機處職責的極度膨脹。
最後是第八章,描述的是軍機處權力達到巔峰之後和珅的專擅以及1799—1820年嘉慶改革。軍機處的一些方面得以改革,但進程受限,嘉慶朝以降軍機處基本上沒有變化。關於軍機處這一新的行政與決策的議事機構對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的影響,我本想做詳細考察,但這裏只能是概述。需要另一本書來描述19世紀的軍機處,揭示在1911年5月它被撤銷前所發揮的作用。將來的研究可能揭示特別班子的傳統(council traditions)通過什麼方式塑造了現今中國的政府和官僚。
並非所有的讀者都會對第一部分的細節感興趣,許多人會直接翻到第二部分,這部分描述的是18世紀成熟的軍機處。與第一部分集中論述短暫的十三年不同,第二部分包括乾隆皇帝在位的六十年,另加禪位後的三年,因此不能刻畫太細。作為導言性質的第五章,敍述了雍正時期三個非正式內廷機構在服喪期合併為過渡性的“總理事務王大臣”,並解釋了雍正時期的一個內廷機構的名稱“軍機處”如何在乾隆初年再次被使用,作為新的擴大了的內廷機構的名稱,之後這一機構被譯作“Grand Council”是合適的。接下來的第六章和第七章,探討的是乾隆皇帝統治六十多年間的軍機處。這裏對軍機處的發展做了一些敍述,但對於它成長過程中的迂回曲折則少有細節描述。這幾章主要用力之處是要表明中央政府文牘事宜劇增,以及由此帶來的乾隆時期軍機處職責的極度膨脹。
最後是第八章,描述的是軍機處權力達到巔峰之後和珅的專擅以及1799—1820年嘉慶改革。軍機處的一些方面得以改革,但進程受限,嘉慶朝以降軍機處基本上沒有變化。關於軍機處這一新的行政與決策的議事機構對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的影響,我本想做詳細考察,但這裏只能是概述。需要另一本書來描述19世紀的軍機處,揭示在1911年5月它被撤銷前所發揮的作用。將來的研究可能揭示特別班子的傳統(council traditions)通過什麼方式塑造了現今中國的政府和官僚。
資料
清朝軍機處的大量檔案保存了下來,這對中國歷代樞密班子來說絕無僅有。在我研究的過程中,北京和臺北所存大量的清朝檔案得到了整理,並向外國人開放。我開始所做的研究,主題與軍機處稍有差別,我使用了臺北“故宮博物院”編目做得很好的軍機處檔案。就在我將要完成工作的時候,由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教授率領的學者代表團正在考察大陸的檔案館。結果,第二年這裏的部分寶藏向外國人開放,我前往北京的申請得到了批准。
在北京,我所面對的是檔案的海洋,數目是我先前在臺北做研究時的十倍。我認識到,令人瞠目的眾多新檔案使撰寫18世紀君主個人專制統治向軍機處管理轉變(monarchicalconciliar transition)的研究成為可能,這段歷史在臺北的檔案中模糊不清。最後,我重新調整了主題,寫了一本幾乎全新的書。
北京的檔案數量龐大,利用也困難。1980—1981年時,檔案館規定不允許有研究助手,複印和製成縮微膠片也非易事。我不得不手抄任何可能有用的檔案,最後要用中文撰寫所抄檔案的摘由上報檔案館。我上報的摘由有108頁之多!1985年下半年,我再次造訪檔案館,很高興看到檔案的利用條件大有改觀,但因時間短促,不能一一檢視新近能看的浩瀚材料。結果,因這兩次檔案館之行,我不得不將研究限於臺北檔案涉及不多的軍機處歷史時段——主要是雍正晚期和乾隆早期(約1728—1760)。即便是這些年份也只能有所割捨,同時我不情願但又不得不忽略北京所藏其他大部分年份的檔案。這種專注使我可以對軍機處的形成期做透徹的研究——下限約為乾隆二十五年(1760),這個時候新的議事制度得以形成——但對乾隆皇帝統治的剩餘年份著墨較少。
北京的檔案對於本書的研究誠然重要,但僅僅依靠一地的檔案還不夠。儘管早在18世紀軍機處有著錄副甚至是有三份副本(甚至更多)的做法,然而臺北和北京都有數種各自獨有的檔案。若無兩地的關鍵檔案,本書是無法著筆的。
研究軍機處必須利用檔案。已出版的原始資料未能講述軍機處的來龍去脈。軍機處早期的成長,部分為內廷的保密性遮蔽,後來的研究者看不清它的發展。保密的做法在19世紀還很盛行。作為一個正式條目,軍機處最終收入了1818年的《嘉慶會典》和《嘉慶會典事例》,《嘉慶會典》對軍機處有簡短的描述,而《嘉慶會典事例》則幾乎付諸闕如。
軍機大臣也保守著軍機處的秘密。已出版的軍機大臣自傳性質的著述和奏疏彙編,比如張廷玉(1672—1755)、阿桂(1717—1797)的著作都對軍機處重要活動資訊略而不載,從而保守了機密。以張廷玉的自訂年譜為例,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才提到這一由大臣所組成的集團,而這已是它建立兩年多之後了,儘管這一時期張廷玉一直密切地參與其中業務。而且,18世紀的一些軍機章京(如王昶,尤其是趙翼)留下了關於軍機處業務流程有價值的記述,但他們很顯然也自我審查,避開敏感的資訊。軍機章京梁章钜(1775—1849)廣泛收集已有資料,於1882年纂成了關於軍機處歷史和業務流程的著作《樞垣記略》,但可能也存在類似問題。梁章钜接觸到了軍機處大量的檔案,然而他的整個資料具有高度選擇性。近年來,一些學者利用了邊緣人物如席吳鏊、葉鳳毛的片斷回憶材料,此二人曾對軍機處前身的一些活動做了有限的觀察,並在多年後記述了軍機處的起源。但是,經與檔案證據比對,可以證實這些回憶只有部分是準確的,而有的甚至完全令人走入歧途。對這些材料的依賴有時令現代學者偏離了軌道,徒添對雍正時期研究的困難。我的研究重點放在雍正皇帝忠誠的弟弟怡親王允祥和戶部大臣所起的作用上,他們是雍正朝內廷重要的促成因素,這一點是從檔案資料中得出的,而這些檔案資料要比那些模糊回憶的作者刊行他們觀察所得的時間早許多。
18世紀軍機處的檔數以萬計,每年所產生的滿漢文檔案可能有數千件之多;不消說,即便是能接觸到這些材料,我也不可能將它們讀完。因此,在許多問題上,我已盡力對材料做了概述,以適應現代學術出版的篇幅要求。我看到了對於研究軍機處有用的大量公文,包括奏摺——以原件即朱批奏摺形式保存著,還有奏摺的抄件即錄副奏摺,以及各種檔冊。與此前相比,所有這些檔案為軍機處研究提供了更細緻、更直接的資料。
雍正朝有一種極不尋常的文獻保留至今:皇帝親筆批示的大量奏摺,批示用皇帝專屬的顏色——朱紅色書寫。雍正皇帝在批示時,常常心理不設防,將他的想法自然吐露給他最信任的一些人。有些批示長達數頁,等於是“意識流”信件。我們今天讀到這些,仿佛雍正皇帝正在對我們直接說話,沒有敷衍之詞。而我們還沒有看到帝制中國的任何其他統治者有如此大量的自我表露的東西。
雍正皇帝的材料常常揭示他的所思所想,但這些證據也有使用上的困難。雍正皇帝的行事風格時常混亂無序——為此,我設立了一種卡片,名為“雍正混亂無序”(Yungcheng chaos)。此類檔所抄錄的內容,顯示出雍正皇帝對統治認真、狂熱關注的背後,處處是偏愛獨立處理政務,時常隨意甚或任性。例如,雍正皇帝常常在奏摺上書寫決定,然後該折就返給具奏人,因而京中的檔案對此未留任何記載。為瞭解皇帝這些隻言片語,高級輔助官員們很快就創立了一些方法,這樣做不足為異。“雍正混亂無序”檔所表現出的又一特色,是雍正皇帝喜愛用不同的字眼指稱同一事物,或是用同一個詞表示不同的事物。熟悉雍正材料的研究者不會奇怪,何以在乾隆皇帝統治伊始,官員們就要通過建立更嚴格的程式對此加以彌補。
乾隆和嘉慶朝的檔案材料發生了變化。儘管比雍正朝更為完整,檔冊更多,但這兩個時期的材料缺少了雍正材料中皇帝許多自然流露的心底話。因此,與雍正皇帝長篇累牘一吐肺腑、開誠佈公不同,乾隆皇帝的批語通常精練且格式化,這一事實反映出新的乾隆朝一開始就正規化了。結果,研究者再不能看到雍正皇帝朱批所揭示資訊的那種引人入勝,聊以寬慰的是,這時資訊總量在增多。
乾隆時期的另一個現象是軍機處活動範圍不斷擴大,這可以從方略館的檔案數量窺得一二。這些檔案展現了由軍機處直接管理的檔案和史書編纂機構的運作及發展。方略館這一新出版機構在刊行許多方略之前,能夠審查(同意、修飾或查禁)原始檔案,在乾隆時期刊印了數目特別巨大的方略,以歌頌清朝的開疆拓土。軍機處也負責前幾朝遺留下的一些出版事宜。另有一些檔案是有關軍機處滿伴的,直到現在人們還未注意到這一集團的活動,可能是普遍認為,清朝確實如它所宣稱的那樣實行了不偏不倚的滿漢複職制。內閣對於題本票擬的指導性冊籍(如“票部本式樣”)反映出,內閣和六部官僚化的程度是以前所想像不到的,上面有上千條的細節規定,沒有給上傳下達或是擬定決策留多少獨立行事的空間。在北京的檔案館,我也翻閱了軍機處自己庋藏的檔案,檔案目錄表明了軍機處職責範圍的日益變化。檔案中有官僚文書往來,開啟了觀察中層官僚活動的領域,而這一層次的官僚迄今基本上還沒有進入研究者的視野。
在本研究關涉的整個時期,軍機大臣所寫的奏片是為了向皇帝解釋說明情況,而它在20世紀,對於我這個心懷感激的研究者來說起著同樣的作用。
在北京,我所面對的是檔案的海洋,數目是我先前在臺北做研究時的十倍。我認識到,令人瞠目的眾多新檔案使撰寫18世紀君主個人專制統治向軍機處管理轉變(monarchicalconciliar transition)的研究成為可能,這段歷史在臺北的檔案中模糊不清。最後,我重新調整了主題,寫了一本幾乎全新的書。
北京的檔案數量龐大,利用也困難。1980—1981年時,檔案館規定不允許有研究助手,複印和製成縮微膠片也非易事。我不得不手抄任何可能有用的檔案,最後要用中文撰寫所抄檔案的摘由上報檔案館。我上報的摘由有108頁之多!1985年下半年,我再次造訪檔案館,很高興看到檔案的利用條件大有改觀,但因時間短促,不能一一檢視新近能看的浩瀚材料。結果,因這兩次檔案館之行,我不得不將研究限於臺北檔案涉及不多的軍機處歷史時段——主要是雍正晚期和乾隆早期(約1728—1760)。即便是這些年份也只能有所割捨,同時我不情願但又不得不忽略北京所藏其他大部分年份的檔案。這種專注使我可以對軍機處的形成期做透徹的研究——下限約為乾隆二十五年(1760),這個時候新的議事制度得以形成——但對乾隆皇帝統治的剩餘年份著墨較少。
北京的檔案對於本書的研究誠然重要,但僅僅依靠一地的檔案還不夠。儘管早在18世紀軍機處有著錄副甚至是有三份副本(甚至更多)的做法,然而臺北和北京都有數種各自獨有的檔案。若無兩地的關鍵檔案,本書是無法著筆的。
研究軍機處必須利用檔案。已出版的原始資料未能講述軍機處的來龍去脈。軍機處早期的成長,部分為內廷的保密性遮蔽,後來的研究者看不清它的發展。保密的做法在19世紀還很盛行。作為一個正式條目,軍機處最終收入了1818年的《嘉慶會典》和《嘉慶會典事例》,《嘉慶會典》對軍機處有簡短的描述,而《嘉慶會典事例》則幾乎付諸闕如。
軍機大臣也保守著軍機處的秘密。已出版的軍機大臣自傳性質的著述和奏疏彙編,比如張廷玉(1672—1755)、阿桂(1717—1797)的著作都對軍機處重要活動資訊略而不載,從而保守了機密。以張廷玉的自訂年譜為例,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才提到這一由大臣所組成的集團,而這已是它建立兩年多之後了,儘管這一時期張廷玉一直密切地參與其中業務。而且,18世紀的一些軍機章京(如王昶,尤其是趙翼)留下了關於軍機處業務流程有價值的記述,但他們很顯然也自我審查,避開敏感的資訊。軍機章京梁章钜(1775—1849)廣泛收集已有資料,於1882年纂成了關於軍機處歷史和業務流程的著作《樞垣記略》,但可能也存在類似問題。梁章钜接觸到了軍機處大量的檔案,然而他的整個資料具有高度選擇性。近年來,一些學者利用了邊緣人物如席吳鏊、葉鳳毛的片斷回憶材料,此二人曾對軍機處前身的一些活動做了有限的觀察,並在多年後記述了軍機處的起源。但是,經與檔案證據比對,可以證實這些回憶只有部分是準確的,而有的甚至完全令人走入歧途。對這些材料的依賴有時令現代學者偏離了軌道,徒添對雍正時期研究的困難。我的研究重點放在雍正皇帝忠誠的弟弟怡親王允祥和戶部大臣所起的作用上,他們是雍正朝內廷重要的促成因素,這一點是從檔案資料中得出的,而這些檔案資料要比那些模糊回憶的作者刊行他們觀察所得的時間早許多。
18世紀軍機處的檔數以萬計,每年所產生的滿漢文檔案可能有數千件之多;不消說,即便是能接觸到這些材料,我也不可能將它們讀完。因此,在許多問題上,我已盡力對材料做了概述,以適應現代學術出版的篇幅要求。我看到了對於研究軍機處有用的大量公文,包括奏摺——以原件即朱批奏摺形式保存著,還有奏摺的抄件即錄副奏摺,以及各種檔冊。與此前相比,所有這些檔案為軍機處研究提供了更細緻、更直接的資料。
雍正朝有一種極不尋常的文獻保留至今:皇帝親筆批示的大量奏摺,批示用皇帝專屬的顏色——朱紅色書寫。雍正皇帝在批示時,常常心理不設防,將他的想法自然吐露給他最信任的一些人。有些批示長達數頁,等於是“意識流”信件。我們今天讀到這些,仿佛雍正皇帝正在對我們直接說話,沒有敷衍之詞。而我們還沒有看到帝制中國的任何其他統治者有如此大量的自我表露的東西。
雍正皇帝的材料常常揭示他的所思所想,但這些證據也有使用上的困難。雍正皇帝的行事風格時常混亂無序——為此,我設立了一種卡片,名為“雍正混亂無序”(Yungcheng chaos)。此類檔所抄錄的內容,顯示出雍正皇帝對統治認真、狂熱關注的背後,處處是偏愛獨立處理政務,時常隨意甚或任性。例如,雍正皇帝常常在奏摺上書寫決定,然後該折就返給具奏人,因而京中的檔案對此未留任何記載。為瞭解皇帝這些隻言片語,高級輔助官員們很快就創立了一些方法,這樣做不足為異。“雍正混亂無序”檔所表現出的又一特色,是雍正皇帝喜愛用不同的字眼指稱同一事物,或是用同一個詞表示不同的事物。熟悉雍正材料的研究者不會奇怪,何以在乾隆皇帝統治伊始,官員們就要通過建立更嚴格的程式對此加以彌補。
乾隆和嘉慶朝的檔案材料發生了變化。儘管比雍正朝更為完整,檔冊更多,但這兩個時期的材料缺少了雍正材料中皇帝許多自然流露的心底話。因此,與雍正皇帝長篇累牘一吐肺腑、開誠佈公不同,乾隆皇帝的批語通常精練且格式化,這一事實反映出新的乾隆朝一開始就正規化了。結果,研究者再不能看到雍正皇帝朱批所揭示資訊的那種引人入勝,聊以寬慰的是,這時資訊總量在增多。
乾隆時期的另一個現象是軍機處活動範圍不斷擴大,這可以從方略館的檔案數量窺得一二。這些檔案展現了由軍機處直接管理的檔案和史書編纂機構的運作及發展。方略館這一新出版機構在刊行許多方略之前,能夠審查(同意、修飾或查禁)原始檔案,在乾隆時期刊印了數目特別巨大的方略,以歌頌清朝的開疆拓土。軍機處也負責前幾朝遺留下的一些出版事宜。另有一些檔案是有關軍機處滿伴的,直到現在人們還未注意到這一集團的活動,可能是普遍認為,清朝確實如它所宣稱的那樣實行了不偏不倚的滿漢複職制。內閣對於題本票擬的指導性冊籍(如“票部本式樣”)反映出,內閣和六部官僚化的程度是以前所想像不到的,上面有上千條的細節規定,沒有給上傳下達或是擬定決策留多少獨立行事的空間。在北京的檔案館,我也翻閱了軍機處自己庋藏的檔案,檔案目錄表明了軍機處職責範圍的日益變化。檔案中有官僚文書往來,開啟了觀察中層官僚活動的領域,而這一層次的官僚迄今基本上還沒有進入研究者的視野。
在本研究關涉的整個時期,軍機大臣所寫的奏片是為了向皇帝解釋說明情況,而它在20世紀,對於我這個心懷感激的研究者來說起著同樣的作用。
書評
研究清朝制度史的中外著述中,《君主與大臣》是最優秀的成果。
——何炳棣(芝加哥大學教授)
研究清朝制度史的中外著述中,《君主與大臣》是最優秀的成果。
——何炳棣(芝加哥大學教授)
這是對於清史研究技藝以及清朝歷史都有貢獻的重要著作。……《君主與大臣》一書的價值,不僅在於它所取得的成就,而且也在於它代表的新的研究方向。……在未來許多年,它將是18世紀歷史研究的標杆作品。
——蓋博堅(華盛頓大學教授)
——蓋博堅(華盛頓大學教授)
《君主與大臣》是難得一見的著作,博得交口稱譽,且取得學術突破。
——戴廷傑(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戴廷傑(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在西方,沒有人比白彬菊教授更熟悉清朝的檔案。《君主與大臣》一書,使用第一手確鑿材料,為我們提供了對於帝制中國內部決策的認識。關於軍機處(對中國皇帝而言,大致相當於美國總統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建立的原因,學界爭論不休。白彬菊的研究對此提出了新看法,同時揭示了清朝君主政體是以人們意想不到的方式運作的。
——魏斐德(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
——魏斐德(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
《君主與大臣》一書,會讓認為制度史單調乏味的人手不釋卷。
——司徒琳(印第安那大學教授)
——司徒琳(印第安那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