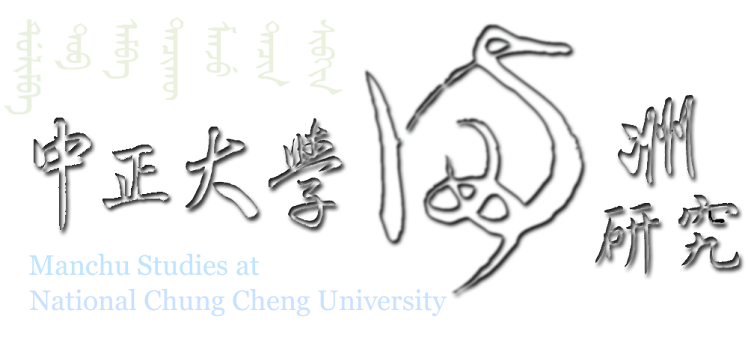(圖:拉薩布達拉宮內的六世達賴像)
1792年乾隆帝御筆親書的漢文版《喇嘛說》(雍和宮御碑亭有滿、漢、蒙、藏碑文),稱藏傳佛教為「喇嘛教」及「黃教」,雖有些內容並不準確,例如說「創教」者為元朝時候薩迦教派(Sa skya pa)的法王八思巴('Phags pa)等,都跟史實不符,但對滿清支持藏傳佛教和頒敕印給達賴與班禪兩位活佛的動機,卻說得絕不含糊:「蓋中外黃教總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歸之,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繫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諂敬番僧也。…若我朝之興黃教則大不然,蓋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護之,以為懷柔之道而已。」
自從威震兩百年的西藏吐蕃王朝於九世紀覆亡後,青藏高原上政權四分五裂,十一世紀開始各佛教教派結合地方豪強進行統治,但再無出現統一整個高原的政權,藏族勢力也再沒有能力伸展至高原以外。清朝統治者以外族身份從東北入主中原,清楚知道高原上的藏人對其江山並無威脅性,怕的是實際控制藏地的蒙古王公們。蒙古各部在北面和西北虎視眈眈,若夥同青藏高原的藏人一併作反,大清江山肯定岌岌可危。清廷一方面盡量分散和鉗制蒙古王公的強大勢力,一方面利用藏傳佛教及其高僧籠絡蒙古。西藏在這表面籠絡而暗中較勁的三角關係中如履薄冰,設法求存,但縱使步步為營,由於處於滿蒙勢力的夾縫,進退維艱。被後世稱為於十七世紀統一藏地的藏傳佛教格魯派首領第五世達賴喇嘛雖然以過人的聲望才智穩住局面,但他的繼任人第六世達賴既無他的政治才智,更被指縱情酒色,終於成為藏滿蒙政治角力的犧牲品,落得被蒙古押解往北京而死於青海湖畔的下場,成為其中一名短命的傀儡達賴。如果不是留下傳誦至今的幾十首膾炙人口、動人心弦的詩歌,有誰會特別留意他!
蒙古在藏地的勢力,始自十三世紀初蒙古汗國崛起的時代。十三世紀是一個紛亂的時代,藏傳佛教各宗派為了在環境嚴苛的高原上爭奪資源和拓展地盤,互相傾軋,內鬥不斷。為了鞏固勢力,各自依附不同的蒙古王公,以「施主與福田」的名義建立「供施關係」,尋找軍事靠山。1247年,藏傳佛教薩迦派第四祖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Sa skya Paṇḍita dKun dga’ rgyal mtshan)被蒙古闊端(Kőden)召往涼州,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代表藏地各宗派歸順。忽必烈即帝後,奉薩迦派第五祖八思巴為國師。1265年,久居蒙古的八思巴返回後藏薩迦,元朝正式實行對藏地的管治。元朝覆亡以後,雖然蒙古勢力退出中原,但蒙古各部仍盤踞漠北漠西一帶,青藏高原仍留下很多蒙古軍兵。有明一代,蒙古的威脅時刻存在。十五世紀後半葉至晚期,退居漠北的蒙古各部再趨強大。其中瓦剌(Oyirad, 元代亦譯作斡亦剌,清則譯作衛拉特、厄魯特)遷於今日新疆一帶,分為準噶爾(J̌egün γar)、土爾扈特(Torγud)、杜爾伯特(Dőrbed)、和碩特(Qošod)四部。十七世紀中葉明清交接時,藏地各方勢力又再依附不同的蒙古王公,展開角力,形成藏地的實際管治者其實是蒙古這一鮮為人留意的局面。蒙古與滿洲勢均力敵,甚至可能處於優勢,對清朝威脅極大。對同是塞外民族,曾經入主中原並橫跨歐亞的蒙古人,清廷極度顧忌。有說法是清初以蒙古王公代理管治西藏,但這其實是晚明以來的既成局面, 而並非清廷所願。
蒙古人崇信藏傳佛教,亦是始自十三世紀元蒙時代。忽必烈尊八思巴為國師與帝師,並不全是籠絡策略,也有基於信徒對上師的虔敬。成書於十四世紀初的藏文《鄔堅巴大成就者傳記》有記載忽必烈晚年對由藏地前往元都的噶舉派(bKa’ brgyud pa)高僧鄔堅巴(U rgyan pa Rin chen dpal)的禮待,及對朝中強橫薩迦派僧人的順從。元朝縱容藏僧專橫之事,明代筆記和乾隆御製《喇嘛說》也有提及。元亡後,藏傳佛教在蒙古族中曾沉寂下來,藏蒙關係淡泊,及至十六世紀中葉才再度緊密起來。藏傳佛教格魯派(dGe lugs pa)開創人宗喀巴(rJe Cong kha pa)的弟子索南嘉措(bSod nams rgya mtsho, 1543-1588),因為教派屢遭當時由帕竹噶舉教派撐腰的藏巴(gTsang pa)政權打壓,於是靠攏當時大肆擴張勢力並經常侵擾明朝的蒙古土默特部首領阿勒坦汗(Altan Qan,有譯作俺答汗,1507-1582),獲阿勒坦汗給予「達賴」(Dalai)尊號,即蒙語「海洋」之意。後世奉為「第三世達賴」,分別以宗喀巴較早的兩名弟子為一世與二世。為了與蒙古人有更緊密的關係,格魯派第三世達賴圓寂後,弟子們根據其遺囑認定阿勒坦汗的孫兒為其轉世靈童,奉為四世達賴 。這位蒙古族的達賴,體現了活佛轉世制度深刻的政治含義,正如《蒙古佛教史》(頁73)所言:「西藏佛教的活佛轉世制度的發展和形成,實際上是把世俗的世襲制度成功而巧妙地向佛教聖職移植的新的組織形式,也可以說它的形式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宗教領袖人物所採取的一種政治方法。」。
但是,有蒙古土默特部作靠山也不一定萬全,縱使四世達賴是蒙古人,仍然因為得罪統治前後藏的藏巴政權而不得善終,死時只有27歲,藏巴政權還下令格魯派不准找尋其靈童。幾經波折,來自山南藏族的五世達賴洛桑嘉措(Blo bzang rgya mtsho, 1617-1682)才得以繼位。五世達賴精明能幹,親政後投靠蒙古和碩特部的首領固始汗(Güüši Qan, 1582-1654),得其扶持推翻藏巴汗,登上前後藏統治者的地位。與此同時,固始汗又給予宗喀巴另一弟子「班禪博克多」的尊號(「班禪」Pan chen 為藏語「大學者」之意,「博克多」為蒙語「睿智英武」之意),是為第四世班禪,追奉前人為一至三世。達賴與班禪兩大活佛系統得以確立,蒙古王公居功至偉。
五世達賴是少數確掌實權的達賴之一。雖然一般說「政教合一」是由他開始,其實當時他頂頭還有蒙古,固始汗才是西藏的幕後統治者。五世達賴執政至65歲才圓寂,時為1682年,康熙21年。當時支持他的固始汗早已逝世,其後人早已想伺機收回政權。五世達賴雄才偉略,在世時仍能勉力於藏滿蒙角力的漩渦中站穩,但如果圓寂消息傳出,形勢便很不妙。他生前苦心培養的攝政第巴桑結(sDe pa Sangs rgyas)恐清廷和蒙古人知道後會乘機找麻煩,秘不發喪,假稱五世閉關,找人假冒他,瞞住內面大部分人和外面所有人,在藏南雖然秘密找到靈童,但沒迎進布達拉宮, 然後攝政用五世名義獨攬政權達十五年之久。
第六世達賴倉央嘉措(Tshangs dbyangs rgya mtsho, 1683-1706)出生於藏南門隅(Mon yul)地區,但這「藏南」其實位於今日印度實際控制的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1931年,英屬印度單方面將藏南大約3萬(有說6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劃歸印度,這邊界線稱為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當時西藏噶廈政府同意此劃分,但中華民國不承認這條分界線。1962年的中印邊境戰爭,是因為解放軍進入西藏後與印度領土接壤而產生問題,會談破裂而起。一般說倉央嘉措屬藏南門巴(Mon pa)族,而根據今日中國少數民族的劃分,門巴族是藏族以外的一個少數民族,不屬於藏族。為何五世達賴的繼承人會在此被尋獲?
如前所說,藏傳佛教各派歷來都不斷拓展地盤,爭奪資源。藏南的深山一直都是佛法不太盛的地方,人民主要信奉苯教和跟苯教很多共通處的早期藏傳佛教寧瑪派教法,倉央嘉措正是來自一個信奉寧瑪派的家庭。十三、四世紀藏地傳記經常提到高僧們不畏艱苦率領徒眾到這一帶未開化的地方弘法。格魯派得勢後,曾令不少其他宗派的寺院改宗,當然也會向這裡拓展勢力。1680年,門隅地區的寧瑪派(rNying ma pa)達旺寺(rTa dbang)改宗格魯派,之後亦有其他寧瑪派寺院改宗格魯。第六世達賴在此出生,門巴族一帶的喜馬拉雅南麓便順理成章成為格魯派的地盤,大抵跟四世達賴轉生到蒙古族中去的政治目的相近。
有說是康熙帝親征準噶爾時從軍中聽來消息才揭發五世達賴已死的真相。康熙帝是極強勢和精明的君主,謊言是否真的成功瞞過他十五年?看來未必,之前大清江山仍未完全穩固,暫且裝聾扮啞,待成功出征漠北才揭破謊言也有可能。而康熙帝首次親征準噶爾期間,西藏與蒙古雖未至外合,卻裡通,洩漏清廷虛實給蒙古人知道,康熙帝對西藏的不滿可想而知。1697年(康熙36年),康熙帝遣使往拉薩,命攝政第巴桑結使五世達賴與清廷使臣相見,攝政才被迫坦白,並從藏南迎接已經十四歲的六世達賴至拉薩,剃髮受戒,接受密集式宗教灌頂和教育。但是,慣於藏南山野間生活的倉央嘉措不久便厭倦了這枯燥的苦學生活,愛上詩律和修辭,開始通過詩歌抒發對愛情的渴望,以民歌樸實和自由語句表達其感情,有回憶在藏南與姑娘們兩小無猜、情竇初開的詩歌,有描述來到拉薩後與民間姑娘如何眉來眼去、同床共枕,也有描述修行時心猿意馬。他曾努力想潛心修佛。可惜並不成功。二十歲時, 攝政桑結敦請他到後藏日喀則班禪喇嘛跟前受比丘戒,倉央嘉措不但不接受,還要放棄之前所受的較低的沙彌戒,以死要挾,與攝政鬧翻。據說他從此留長髪,脫下黃色僧袍,穿錦繡衣裝,常在布達拉宮山後新建的林苑作樂,在有女子陪酒的酒館喝得醉醺醺引吭高歌。初時怕人知曉,悄悄夜間溜出布達拉宮,後來膽子越來越大,毫不避忌。
當時被藏人稱為「拉藏巴」(Lha tshangs pa,有作「拉藏汗」)的固始汗曾孫和伊犁的厄魯特王為爭奪西藏政權,欲剷除攝政,並不承認倉央嘉措為達賴。但倉央嘉措毫不抗爭,在班禪喇嘛面前聲明寧放棄格魯派教主的尊位,並公然花天酒地,清廷和拉藏巴、蒙古王公等多次警告他都置若罔聞。攝政第巴桑結兩次想毒殺蒙古拉藏巴,並曾想用武力驅逐他出拉薩,都不成功,六世達賴處境非常不妙。拉藏巴率兵攻攝政桑結府邸,桑結逃亡,後被殺。六世達賴活在政治夾縫中,放縱行為予人口實,拉藏巴欲廢他,遂取得清帝詔書,以「不守清規」、「非真達賴」等理由將他逮捕。他最終成為十八世紀初藏滿蒙三地政治角力與鬥爭的犧牲品。按漢地文獻記載,他是解往內地途中在青海湖畔突患水腫去世,結束了悲情的短暫人生,時年二十三歲。
-------------------------------------
李惠玲( Brenda Li) , 牛津大學西藏及喜馬拉雅研究博士 (D.Phil.,Tibetan and Himalayan Studies, Oxford University),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西藏語文導師,著有《細說西藏歷史文化》、《鄔堅巴評傳:十三世紀藏地大成就者》二書及其他論文、譯著。